3 象形的字
- 目录
- 0 登高丘·望远海
- 1 字的黎明
- 新石器时代的矛盾
- 灿烂的图像
- 2 造字的困境暨文字生产线的出现
- 象形字的终点
- 回归声音与实像的坚持
- 造字的最终解答
- 2 造字的困境暨文字生产线的出现
- 把肉汁封存起来
- 不革命的文字系统
- 以古埃及文字为例
- 文字和语言的分离
- 以颜色为例
- 一个最美丽的形声字
- 3 象形的字
- 3 象形的字
- 老材料与新造字
- 从脚印开始
- 共同记忆
- 文字密码
- 愈来愈难解码的文字
- 莫奈的眼睛
- 非现实之物的现实主义
- 4 指事的字及其他抽象符号
- 曲线式指事符号
- 小点的三态变化
- 传送到耳朵和皮肤之字
- 眼睛的错觉之字
- 5 转注·假借·不再创造的新文字
- 转注的意义延伸
- 假借的意义跳跃
- 5 转注·假借·不再创造的新文字
- 不再造字的两大主角
- 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匠”
- 有钉痕的文字
- 6 找寻甲骨文里的第一枚时钟
- 最先看到太阳
- 失败之道
- 谁需要什么样的时间刻度?
- 6 找寻甲骨文里的第一枚时钟
- 畜牧的故事
- 狩猎的故事
- 什么样的有闲与创造
- 全新表面
- 7 最本雅明的字
- 眼花缭乱
- 感官的位移
- 7 最本雅明的字
- 甲骨文大街
- 百年孤独的游手好闲者
- 8 低贱的字和一页完整的性爱生产图示
- 大道之始的两个象形字
- 逃遁与追赶
- 柳暗花明的故事
- 生产指南
- 8 低贱的字和一页完整的性爱生产图示
- 花的儿女
- 奔者不禁
- 9 可怕的字
- 哀矜勿喜
- 杀老/杀小
- 死者/活者
- 满街奴隶
- 9 可怕的字
- “我”之命名
- 10 奇怪的字
- 随机选择
- 后脚站立的动物王国
- 托尔斯泰的历史图像
- 生病的意符
- 更命运悲惨的意符
- 10 奇怪的字
- 文字的离心力量
- 全世界最美丽的尾巴
- 11 简化的字
- 其实每时每刻在进行
- 埋于自身的种子
- 两种逆向行驶
- 不成立的算术
- 11 简化的字
- 文字与莱布尼茨
- 12 死去的字
- 二十八个有关马的文字
- 海市蜃楼的玉之王国
- 单独命名
- 和权力勾结
- 小说家如是说
- 12 死去的字
- 小说家如是说
- 风露想遗民
- 13 卷土重来的图形字
- 有限文字的真相
- 没文字的喜悦
- 保护保卫自己
- “文”和“字”
- 上一页下一页


























理论上,这应该算是个象形字,摹写的是会让彼时初民惊惧但并非不常见的自然景象,那就是集中于夏日水分暴烈蒸发、乌云密布、即将降下滂沱之雨的天空闪逝画面,由此冻结成文字。其中有雲(云)的符号 (云,雲字的原形),有悍厉撕裂天空的长蛇状闪光,还有三个有趣的
(云,雲字的原形),有悍厉撕裂天空的长蛇状闪光,还有三个有趣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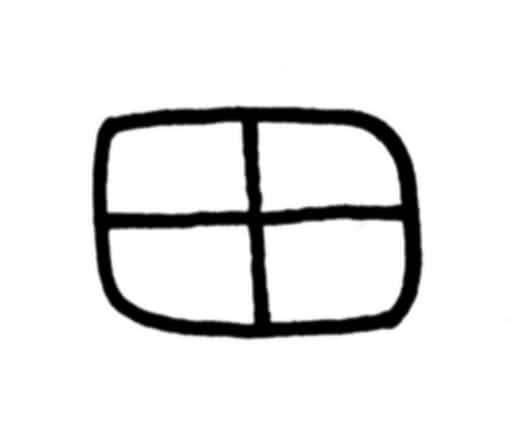 字符号,当然不会是地上的田地忽然跑天上去了,这是这个字最有趣的部分。
字符号,当然不会是地上的田地忽然跑天上去了,这是这个字最有趣的部分。
 (云,雲字的原形),有悍厉撕裂天空的长蛇状闪光,还有三个有趣的
(云,雲字的原形),有悍厉撕裂天空的长蛇状闪光,还有三个有趣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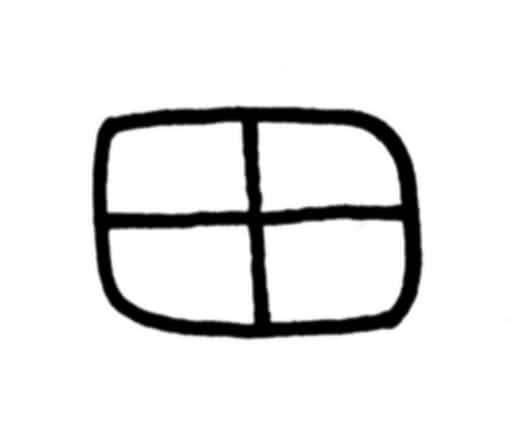 字符号,当然不会是地上的田地忽然跑天上去了,这是这个字最有趣的部分。
字符号,当然不会是地上的田地忽然跑天上去了,这是这个字最有趣的部分。因此,这个字就是“雷”字,会打死人,给牛羊树木带来死亡,也会降下丰沛雨水带来生命,若依卡西尔所主张初民蓦然惊惧深印心间的“瞬间神”概念(卡西尔以为诸神的起源正在于此),它显然还会带来宗教、生命本体的反思及其他。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字更象形更忠于自然景象一点,那甲骨文的确摹写了另一个造型 ,把
,把 这个不易解的符号换成实体性的豆大雨点;如若一定要精准抓住打雷闪电且尚未下雨的山雨欲来的迫人画面(雨一降下,人心的确有随气压改变瞬间纾解宣泄开来的明显感受,如魔咒解除),好聚焦雷电的暴烈,不让雨水模糊了分散了注意力,那甲骨文中还是有另一个我以为更漂亮的造型,
这个不易解的符号换成实体性的豆大雨点;如若一定要精准抓住打雷闪电且尚未下雨的山雨欲来的迫人画面(雨一降下,人心的确有随气压改变瞬间纾解宣泄开来的明显感受,如魔咒解除),好聚焦雷电的暴烈,不让雨水模糊了分散了注意力,那甲骨文中还是有另一个我以为更漂亮的造型, ,其中符号
,其中符号 是不得不有点抽象化的光点瞬间冻结摹写,这招在甲骨文不止一回用到,像我们前面提过的“晶”(
是不得不有点抽象化的光点瞬间冻结摹写,这招在甲骨文不止一回用到,像我们前面提过的“晶”( )和“星”(
)和“星”( )两字,便以此代表星芒或星子。
)两字,便以此代表星芒或星子。
 ,把
,把 这个不易解的符号换成实体性的豆大雨点;如若一定要精准抓住打雷闪电且尚未下雨的山雨欲来的迫人画面(雨一降下,人心的确有随气压改变瞬间纾解宣泄开来的明显感受,如魔咒解除),好聚焦雷电的暴烈,不让雨水模糊了分散了注意力,那甲骨文中还是有另一个我以为更漂亮的造型,
这个不易解的符号换成实体性的豆大雨点;如若一定要精准抓住打雷闪电且尚未下雨的山雨欲来的迫人画面(雨一降下,人心的确有随气压改变瞬间纾解宣泄开来的明显感受,如魔咒解除),好聚焦雷电的暴烈,不让雨水模糊了分散了注意力,那甲骨文中还是有另一个我以为更漂亮的造型, ,其中符号
,其中符号 是不得不有点抽象化的光点瞬间冻结摹写,这招在甲骨文不止一回用到,像我们前面提过的“晶”(
是不得不有点抽象化的光点瞬间冻结摹写,这招在甲骨文不止一回用到,像我们前面提过的“晶”( )和“星”(
)和“星”( )两字,便以此代表星芒或星子。
)两字,便以此代表星芒或星子。这两个用雨点、用闪光的更象形之字,有人讲同样就是“雷”字,也有人硬要区隔开来说这应该是“电”字原形,老实讲这没什么关系,这类同源异字的再分割现象不算少见(比方说以下我们还会看到,“育”和“毓”字也是这样,原来都是女性的生产实况摹写),一般都是因应着后来的需要和实际使用随机而生。
 是什么?如果你去过外双溪乃至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馆应该有机会看到,比方说造字之前的彩陶上头,这就是称之为“雷纹”或“雷鼓文”的图案,和云纹水纹山纹等等一样,先已经图案化了、抽象化了或说几何线条化了,没那么素朴象形。
是什么?如果你去过外双溪乃至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馆应该有机会看到,比方说造字之前的彩陶上头,这就是称之为“雷纹”或“雷鼓文”的图案,和云纹水纹山纹等等一样,先已经图案化了、抽象化了或说几何线条化了,没那么素朴象形。从这里来看,我们还可以不算附会地说, 字中的云纹,似乎也有了图案化的倾向,原本的云字姿态要自然一些舒卷一些,更像它在天空的样子。
字中的云纹,似乎也有了图案化的倾向,原本的云字姿态要自然一些舒卷一些,更像它在天空的样子。
 字中的云纹,似乎也有了图案化的倾向,原本的云字姿态要自然一些舒卷一些,更像它在天空的样子。
字中的云纹,似乎也有了图案化的倾向,原本的云字姿态要自然一些舒卷一些,更像它在天空的样子。也就是说, 这个字,有颇象形的闪电画面,加上半象形半图案化的云纹,再加上已成象征符号的雷纹,这三者古怪拼贴而成,若硬要讲这是个象形字,也是个充满后现代概念的象形字。
这个字,有颇象形的闪电画面,加上半象形半图案化的云纹,再加上已成象征符号的雷纹,这三者古怪拼贴而成,若硬要讲这是个象形字,也是个充满后现代概念的象形字。
 这个字,有颇象形的闪电画面,加上半象形半图案化的云纹,再加上已成象征符号的雷纹,这三者古怪拼贴而成,若硬要讲这是个象形字,也是个充满后现代概念的象形字。
这个字,有颇象形的闪电画面,加上半象形半图案化的云纹,再加上已成象征符号的雷纹,这三者古怪拼贴而成,若硬要讲这是个象形字,也是个充满后现代概念的象形字。这里,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同样出现在天上的字,比上面那个拼贴的“雷”字更是魔幻的、想像的。 ,这是彩虹的“虹”字,中间那尺蠖状的弯弧没问题,和你我看到的一样,但两头的怪东西是什么?有人讲这是龍(龙)的头部写生(龍,
,这是彩虹的“虹”字,中间那尺蠖状的弯弧没问题,和你我看到的一样,但两头的怪东西是什么?有人讲这是龍(龙)的头部写生(龍, ,虽然有人说这是扬子鳄一类生物的变形,有人说是某种恐龙脊椎化石的想像还原,但基本上这已是个很魔幻的象形字了),也就是说,天上的虹,对造字的人来说,是一条巨大的七色两头龙,渴了正低头吸着水。
,虽然有人说这是扬子鳄一类生物的变形,有人说是某种恐龙脊椎化石的想像还原,但基本上这已是个很魔幻的象形字了),也就是说,天上的虹,对造字的人来说,是一条巨大的七色两头龙,渴了正低头吸着水。
 ,这是彩虹的“虹”字,中间那尺蠖状的弯弧没问题,和你我看到的一样,但两头的怪东西是什么?有人讲这是龍(龙)的头部写生(龍,
,这是彩虹的“虹”字,中间那尺蠖状的弯弧没问题,和你我看到的一样,但两头的怪东西是什么?有人讲这是龍(龙)的头部写生(龍, ,虽然有人说这是扬子鳄一类生物的变形,有人说是某种恐龙脊椎化石的想像还原,但基本上这已是个很魔幻的象形字了),也就是说,天上的虹,对造字的人来说,是一条巨大的七色两头龙,渴了正低头吸着水。
,虽然有人说这是扬子鳄一类生物的变形,有人说是某种恐龙脊椎化石的想像还原,但基本上这已是个很魔幻的象形字了),也就是说,天上的虹,对造字的人来说,是一条巨大的七色两头龙,渴了正低头吸着水。正是这样造出来的 字,制约了往后重造的新形声字“虹”,让它以“工”的类似发音,从属于尺蠖所属的“虫”类。于是,在中国的造字心灵中,天上彩虹不是光影折射的自然景观,而是美丽壮阔的生命,是一只时时造访的神圣大龙,比起《圣经》中它是上帝和诺亚老爹的盟誓见证,是人和神灭绝性大战的停战协定兼核子限武谈判,想像力走得更远一些。
字,制约了往后重造的新形声字“虹”,让它以“工”的类似发音,从属于尺蠖所属的“虫”类。于是,在中国的造字心灵中,天上彩虹不是光影折射的自然景观,而是美丽壮阔的生命,是一只时时造访的神圣大龙,比起《圣经》中它是上帝和诺亚老爹的盟誓见证,是人和神灭绝性大战的停战协定兼核子限武谈判,想像力走得更远一些。
 字,制约了往后重造的新形声字“虹”,让它以“工”的类似发音,从属于尺蠖所属的“虫”类。于是,在中国的造字心灵中,天上彩虹不是光影折射的自然景观,而是美丽壮阔的生命,是一只时时造访的神圣大龙,比起《圣经》中它是上帝和诺亚老爹的盟誓见证,是人和神灭绝性大战的停战协定兼核子限武谈判,想像力走得更远一些。
字,制约了往后重造的新形声字“虹”,让它以“工”的类似发音,从属于尺蠖所属的“虫”类。于是,在中国的造字心灵中,天上彩虹不是光影折射的自然景观,而是美丽壮阔的生命,是一只时时造访的神圣大龙,比起《圣经》中它是上帝和诺亚老爹的盟誓见证,是人和神灭绝性大战的停战协定兼核子限武谈判,想像力走得更远一些。但这龙头部分无疑是画虫添头的行为,系来自于想像的眼睛而不是肉体的眼睛,是带着神话传说而来的象形字;或者倒过来讲,是魔幻写实,如哥伦比亚籍的伟大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辩之言:“我的小说(针对人们所指称的所谓‘魔幻写实’),每一行都有写实的基础。”
老材料与新造字
还有没有呢?应该还很不少。
其次,则是结绳记事的应用,像甲骨文的“兹”字作 形,或“系”字,作
形,或“系”字,作 等等,有可能只是绳索织线的直接摹写(我比较相信此说),但也有人坚信这正是昔日结绳记事的符号保留。
等等,有可能只是绳索织线的直接摹写(我比较相信此说),但也有人坚信这正是昔日结绳记事的符号保留。
 形,或“系”字,作
形,或“系”字,作 等等,有可能只是绳索织线的直接摹写(我比较相信此说),但也有人坚信这正是昔日结绳记事的符号保留。
等等,有可能只是绳索织线的直接摹写(我比较相信此说),但也有人坚信这正是昔日结绳记事的符号保留。此外还有“祸”字,仍表现了死亡的意象,而呈 ,注意仍是平板状骨头,而视觉焦点仍是卜状的裂纹。
,注意仍是平板状骨头,而视觉焦点仍是卜状的裂纹。
 ,注意仍是平板状骨头,而视觉焦点仍是卜状的裂纹。
,注意仍是平板状骨头,而视觉焦点仍是卜状的裂纹。比方说,数字的记叙方式,一般认为便来自于古老契刻的记忆,因此“一”画一杠,“二”画两杠,“三”画三杠,“四”呢对不起仍然画四杠而成为 ,到“五”才有了契刻的省时兼易辨识(不必傻傻去数)符号性处理,刻成为
,到“五”才有了契刻的省时兼易辨识(不必傻傻去数)符号性处理,刻成为 ,同理,“六”则刻成为
,同理,“六”则刻成为 www•99lib.net……
www•99lib.net……
 ,到“五”才有了契刻的省时兼易辨识(不必傻傻去数)符号性处理,刻成为
,到“五”才有了契刻的省时兼易辨识(不必傻傻去数)符号性处理,刻成为 ,同理,“六”则刻成为
,同理,“六”则刻成为 www•99lib.net……
www•99lib.net……也因此,有关造字起源的种种猜测,除了不负责任地推给仓颉一人而外,其他还有诸如“契刻说”、“结绳说”、“占卜说”、“八卦说”等等,但我个人宁可相信,这些都是大造字前人们的经历和成果,只要还用得上,都会被纳入造字的工程之中——就实质层面来说,这些成果直接化为建构的材料,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就思维层面来说,这漫长的摸索经历,积淀为记忆,改变了或说整体构成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彼时造字的人们是有备而来,有着为期达数百万年的准备。
这样,我们大概就警觉起来了,象形字绝非简单无意见的造字,也许绝大多数的最终呈现方式,看起来就只是我手写我眼地乖乖摹写自然山川鸟兽虫鱼而已,但这只是因比重关系浮在海面之上羞怯安静的冰山可见部分而已,我们只要稍稍把头往下探,马上就会发现麻烦和危险了:一种狰狞而美丽的麻烦和危险等在那儿,它十分之九的巨大部分藏于水面下,愈是航行于文字海洋的老练水手愈懂得害怕。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甲骨字对骨头的呈现方式。我们谁都看过海盗旗吧,画一个有着三处黑色窟窿和森森白牙的头骨,下面则交叉着两根哑铃状的长骨,应该就是我们为数两百多块骨头中最长的大腿骨部分。
我们就来看“占”“卜”二字。“卜”字先来,它是骨头上出现的裂纹(烧炙的或自然的),呈 。“占”字更好玩,是为
。“占”字更好玩,是为 ,是块状的骨头上的裂纹,再加上“口”的会意,说明还是得有通灵的人一旁解兆,作为神界和人界的翻译者。藏书网
,是块状的骨头上的裂纹,再加上“口”的会意,说明还是得有通灵的人一旁解兆,作为神界和人界的翻译者。藏书网
 。“占”字更好玩,是为
。“占”字更好玩,是为 ,是块状的骨头上的裂纹,再加上“口”的会意,说明还是得有通灵的人一旁解兆,作为神界和人界的翻译者。藏书网
,是块状的骨头上的裂纹,再加上“口”的会意,说明还是得有通灵的人一旁解兆,作为神界和人界的翻译者。藏书网我们先来看两组数字,让数字说话:一、据估计,人类生命史上的所有语言系统,仅仅百分之五产生了文字(当然,你可以说后来这百分之五的子裔主宰了这个星球,遂使文字涵盖着今天绝大部分的地表,并不断造成没文字的人们及其语言死去)。二、语言,存在业已三五百万年了,大自然慷慨给予我们声带,使得声音的有效和持续使用不会太晚于人类的存在时间。但文字从象形开始,却远远不及万年,时间比率最多只有百分之一,在这期间,眼睛可见的自然山川鸟兽虫鱼从未短少过,尽管样子容或有点差异,是什么阻挡了人们“自然而然”去摹写它们呢?或者应该讲,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启示人们要大梦初醒般开始摹写它们呢?
因此,我们或多或少就晓得了“死”字中的亡者为什么长那样子,尤其是 上方的天线状诡异图像,极可能不是骨头的任何树枝状残余,而是添加上去的抽象性裂纹符号,彼时人们一看到这个,便完全明白下面那块就是代表亡者的骨头,而不是木板房屋什么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盗旗式骷髅一般。
上方的天线状诡异图像,极可能不是骨头的任何树枝状残余,而是添加上去的抽象性裂纹符号,彼时人们一看到这个,便完全明白下面那块就是代表亡者的骨头,而不是木板房屋什么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盗旗式骷髅一般。
 上方的天线状诡异图像,极可能不是骨头的任何树枝状残余,而是添加上去的抽象性裂纹符号,彼时人们一看到这个,便完全明白下面那块就是代表亡者的骨头,而不是木板房屋什么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盗旗式骷髅一般。
上方的天线状诡异图像,极可能不是骨头的任何树枝状残余,而是添加上去的抽象性裂纹符号,彼时人们一看到这个,便完全明白下面那块就是代表亡者的骨头,而不是木板房屋什么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盗旗式骷髅一般。其实,正确地来说,人类对自然的摹写并不自象形文字开始,99lib•net而是一种独立的、不与语言接轨的图画。像我们说过彩陶上的图像花纹;像比方说美国西南方纳瓦霍族(没有文字)先民画在新墨西哥州巨大岩壁上,如今被盗猎的白人一块一块切下来运走贩卖的狩猎或仪式图像;或者更有名的,法国南方的拉斯科洞穴壁画,估计距今一万五千年到两万年左右,其中最醒目最漂亮的,是一匹桀骜不驯的橘色大马(橘色,是因为受制于他们的染料颜色),生动且野性淋漓,尽管被猎人追捕,屁股上还插着箭。看它长相,应该就是一匹如假包换的高地马(这是我爱马成痴的女儿教我的)。
答案何在呢?我想,除非彼时的人有着不同于我们的“共识”,皆符号化地认定骨头的表现方式就是这样子。而这个共识又从何而来呢?应该就是来自对骨头使用于占卜行为的熟悉,也就是说,甲骨文的骨头早早放弃了写实,而以甲骨文本身为典故来造字——听起来像个绕口令。
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图像的讯息传递,你得找出最特别、最照眼明白的部分,才能降低“误读”的机率,如果你穷极无聊想用比方说耳朵里某个奇形怪状的小骨头来表现,担保你十个人看有十种答案。
甲骨文的“骨”字不少,大致皆做 形,肉眼第一感几近不可解,但我们来看由此所衍生“死”字的其中一个造型
形,肉眼第一感几近不可解,但我们来看由此所衍生“死”字的其中一个造型 ,左方很清楚是一个哀痛逾恒的跪着的人,低头对着右边的朽骨,用此种方式来表达死亡毋宁是很奇怪的很魔幻的。因为一来时间感十分诡异,人要死成这副德性需要多长时间的剥蚀?不客气来说,左边那个人的哀伤也应该“很人性”地淡漠了才是;二来朽骨的存留,较容易保有的仍是头骨、脊椎、肋骨和四肢部位这些大件的,因此我们可以讲这个死去的人死得极抽象极符号,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死法而不是十九世纪大写实主义的死法。
,左方很清楚是一个哀痛逾恒的跪着的人,低头对着右边的朽骨,用此种方式来表达死亡毋宁是很奇怪的很魔幻的。因为一来时间感十分诡异,人要死成这副德性需要多长时间的剥蚀?不客气来说,左边那个人的哀伤也应该“很人性”地淡漠了才是;二来朽骨的存留,较容易保有的仍是头骨、脊椎、肋骨和四肢部位这些大件的,因此我们可以讲这个死去的人死得极抽象极符号,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死法而不是十九世纪大写实主义的死法。http://www.99lib.net
 形,肉眼第一感几近不可解,但我们来看由此所衍生“死”字的其中一个造型
形,肉眼第一感几近不可解,但我们来看由此所衍生“死”字的其中一个造型 ,左方很清楚是一个哀痛逾恒的跪着的人,低头对着右边的朽骨,用此种方式来表达死亡毋宁是很奇怪的很魔幻的。因为一来时间感十分诡异,人要死成这副德性需要多长时间的剥蚀?不客气来说,左边那个人的哀伤也应该“很人性”地淡漠了才是;二来朽骨的存留,较容易保有的仍是头骨、脊椎、肋骨和四肢部位这些大件的,因此我们可以讲这个死去的人死得极抽象极符号,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死法而不是十九世纪大写实主义的死法。
,左方很清楚是一个哀痛逾恒的跪着的人,低头对着右边的朽骨,用此种方式来表达死亡毋宁是很奇怪的很魔幻的。因为一来时间感十分诡异,人要死成这副德性需要多长时间的剥蚀?不客气来说,左边那个人的哀伤也应该“很人性”地淡漠了才是;二来朽骨的存留,较容易保有的仍是头骨、脊椎、肋骨和四肢部位这些大件的,因此我们可以讲这个死去的人死得极抽象极符号,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死法而不是十九世纪大写实主义的死法。从彩陶上已呈几何线条化的图像,我们可知道其来历的源远流长,因为山、水、云、雷的样子不会一开始就以此种“提炼完成”的成熟美学样态表现出来,而是枝叶细节长时间剥蚀的结果;而纳瓦霍印第安人的岩壁图画和拉斯科的地底洞穴图画更让我们骇异,这些古远美丽的画作绝不是无心的、偶然的。像拉斯科,我曾经看过一部科学影片,是科学家从头记录他们用彼时可能的工具配备,试图穿越时间重建绘图当时的经过种种,这事的艰巨、耗时和危险,可能比其成果更让人印象深刻。人要下到曲折无光的地底洞穴之中,在简陋少量、黯淡冒烟而且火光持续跳动的动物性油脂“照明”之下,用他们事先有备而来、辛苦调制的颜料(包括矿物磨碎提炼的有色颜料,混合了可堪黏附崎岖岩壁上的植物性黏着原料加入的口水云云,而拉斯科洞画的安然存留至今,说明他们的颜料研发成果斐然),这才预谋地,缓慢地,让自己心中那幅灿烂的图像,一九-九-藏-书-网点一滴一丝一毫地浮现于这个无光的奇怪地点。有趣的是,这些宛如锦衣夜行的了不起古老画家却留下了自己的手印,看起来还是ego不小,颇有艺术家的自觉和自恋——无论如何,这绝不可能如今天我们兴之所至,把纸笔拿出来就可以的行为,而是心中蕴蓄着某种炽烈的、宗教一类的强大驱力,才可能一个个难关打通、付诸实践的艰辛大事情。
因此,“雷”字的田形符号是老材料,“虹”字的吸水龙头也是老材料。
从这些简单的事实,我们便该把人无心地、被动地摹写自然的天真图像给弃去,顺带地,我们也应该由此对造字人的基本形象有所调整——他们绝不是初来乍到,如童话中睡美人般睁眼第一次看世界那样的人们,相反的,他们之前已和地球相处了几百万年之久,已经用过非文字式的图像一再摹写过眼前的世界,也知道用绳结或刻痕来封存记忆,因此对某类和某种程度的符号使用并非全然陌生。此外,他们使用语言已有数百万年时间,极可能,也断续思索了几百万年时间。因此,在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和疏疏密密的星空底下,已有他们口传耳闻、代代增添修饰的神话和传说,对他们自身的处境,以及和自然界的关系作了程度不一的猜想、询问甚至相当的“结论”,他们大概也一定有自己的音乐和舞蹈,这是另一种情感和思维的载体和符号云云。是带着这些东西而来、并非两手空空的人们造的字,创造出一种和他们的老语言接轨松紧程度不一的新的符号系统来,而面对造字启动这样未曾有过的新工作,他们势必也像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匠一般,一再回头检视自己已有的各式材料,只要堪用,自然毫不吝惜拿出来用做造字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