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斯塔克掌控全局
第十八章 自动书写
第十八章 自动书写
- 目录
- 序幕
- 第一部 无用的废料
- 第一章 泄密
- 第二章 噩梦
- 第三章 公墓疑云
- 第四章 小镇上的命案
- 第五章 96529Q
- 第六章 大城市里的凶案
- 第一部 无用的废料
- 第七章 执行公务
- 第八章 庞波来访
- 第九章 龌龊鬼来犯
- 第十章 当天深夜
- 第十一章 安兹韦尔
- 第十二章 公寓施暴
- 第十三章 纯粹恐慌
- 第一部 无用的废料
- 第十四章 无用的废料
- 第二部 斯塔克掌控全局
- 第十五章 斯塔克悬疑
- 第十六章 乔治·斯塔克来电
- 第十七章 孪生感应
- 第十八章 自动书写
- 第十九章 斯塔克购物
- 第二部 斯塔克掌控全局
- 第二十章 最后期限
- 第二十一章 斯塔克做主
- 第三部 灵魂的摆渡者驾到
- 第二十二章 赛德潜逃
- 第二十三章 两个电话
- 第二十四章 麻雀到来
- 第二十五章 钢铁马辛
- 第三部 灵魂的摆渡者驾到
- 第二十二章 赛德潜逃
- 第二十三章 两个电话
- 第二十四章 麻雀到来
- 第二十五章 钢铁马辛
- 第二十六章 麻雀在飞
- 尾声
- 后记
- 上一页下一页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是吗?这就会引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两个不同的人怎么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指纹和声波纹,两个不同的婴儿怎么可能有完全一样的瘀青……尤其是在只有一个婴儿碰伤了她的腿的情况下。
回答:不。
麻雀飞起。
“艾克与迈克,他们想法一致。”赛德咕哝道。他伸手圈起他写的最后一行字。
还没到时候。

如果不写,我会死。
他垂下手,直到铅笔尖触及纸页。他的手再度被注入了那种麻木的感觉,仿佛是被浸在非常冰冷、非常清澈的溪水中。
赛德坐起来……但他的手依然紧握着铅笔,被拽着移动。
现在,赛德伏在他的日记本上,手握铅笔,努力想要促成这事发生。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开始越来越觉得自己愚蠢。
铅笔迅速画出一系列像鸟的M形曲线。它停下来,接着又开始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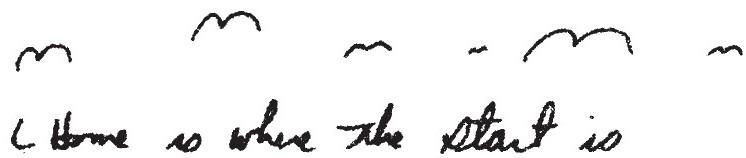
家就在开始的地方。
他的笔迹和以往其他时候都一样,但这些文字是从何而来的呢?肯定不是来自他自己的头脑。此刻除了恐惧和喧嚣的混乱,他的脑子里空无一物。他的手也不再有感觉。他的右臂似乎止于手腕上方的三英寸处。他的手指一点感觉都没有,虽然他可以看到自己正紧握着贝洛牌铅笔,紧得让他的大拇指和前两个手指的指尖都发白了。他仿佛被注射了一针奴佛卡因。
他确实不知道。大概是说真话——或许是部分说真话,至少。她似乎很能看穿他的谎言。
铅笔写道。
回答:因为麻雀又在飞了。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问题:他怎么知道我会在哪里?
“快点。”赛德轻轻地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问题:他看得见你吗?
回答:不,我认为他不知道。
他一直等到丽姿上床后,才上楼去书房。途中,他在他们的卧室门外停了大约一分钟,倾听她均匀的呼吸声,确信她已经睡着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要尝试的事情是否会成功,但如果成功了,那么它可能是危险的,极其危险。
一句双关语。它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之间的联系真的存在,还是他在愚弄自己?关于鸟的事情,他并没有愚弄自己,第一次狂写下来的事情也是真的。他知道这点,但那份炽热和冲动似乎已经减轻了。他的手依然感觉麻木,但这或许与他握笔太紧有关——从他手指侧面的凹印判断,他确实握得非常紧。难道他在那篇关于自动书写的文章里没有读到这样的观点吗?即人们常常用显灵板愚弄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指挥笔写字的不是灵魂,而是操作者的潜意识想法和欲望。
3
问题:他怎么知道我会在哪里?
家在哪里?他望着铅笔沉思,又慢慢将它放到纸上。
它们是真的,他又想。麻雀是真的。那种令人厌恶的莫名恐惧又回来了,不知为何让他感觉很肮脏。他试图握紧拳头,左手的伤口让他疼得叫了出来。止痛药的效力已经过去了。
“哦,我的上帝。”他用颤抖苍白的声音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害怕过……突然,那种脱离肉体的感觉再度充满了他的全身,跟他与斯塔克通电话时感觉到的一样,但现在这种感觉更强烈了,远远更为强烈。
铅笔写道。字迹僵硬、迟疑。铅笔猛地一拉,在他蜡白的手指之间颤抖。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赛德想,它就会折断。
念头闪过后的三个月里,每天十点斯塔克都会敏捷地跳出来,包括周末。他会跳出来,抓住一支贝洛铅笔,开始写他那些癫狂的胡言乱语——这些癫狂的胡言乱语支付了赛德自己的作品所无法支付的账单。接着,书写完后,乔治就会再次消失。
世界充满了麻雀,它们正在等待起飞的指令。
但乔治·斯塔克是他黑暗的另一半吗?他是否曾是他的一部分?自从在斯塔克最后一本小说《驶向巴比伦》的最后一页底部写下“完”后,除了在记忆丧失、恍惚的状态下,他没有用过这些铅笔,甚至没有用它们做过笔记。
但他怀疑自己的意愿无关紧要。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他触动了自身某种可怕的超自然能力,但他却无法控制它。在这件事上,控制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他已经写到了第一张纸的底端。他用麻木的手把它翻过来,用麻木的手掌将它抚平,又开始写起来。
问题:鸟是我的吗?
他盯着瑞明顿牌打字机看了一会儿,它被罩子罩着,不锈钢回车杆从左边戳出来,好像要求搭车者竖起的大拇指。他坐在打字机前,手指不安地敲着桌沿,然后拉开打字机左边的抽屉。
回答:不。他说他不知道,我相信他。
它们飞着,在一阵翅膀的拍打声中远去。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至少现在还不能回答。并且一次失败的尝试就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是的。当斯塔克想被监听时,他打电话到家里来,当他不想被监听时,他就打电话去戴夫市场。首先,他为什么要让人偷听呢?因为他知道警察会监听,他想把一条信息传给警察——即他不是乔治·斯塔克,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以及他已经杀完人了,赛德和他的家人不是他的目标。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想让赛德看看声波纹,他知道警察会进行声波纹比较。他知道警察不会相信他们的证据,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无可辩驳……但赛德会相信的。
斯塔克知道有些什么。但威廉一定也知道有些什么——如果他的腿上有瘀青,肯定会疼的。温迪摔下楼梯时给了他一块瘀青。威廉只知道他有一个痛处。
哦,但早晨它会非常疼的,伙计……而且你要怎么跟丽姿说呢?
米里亚姆·考利张嘴想叫。我就站在门里,耐心地等待了四个多小时,没有喝咖啡,没有抽香烟(我倒是想抽一支烟,事情一结束我就会来上一支,但完事之前,烟味可能会让她警觉)。我提醒自己,割断她的喉咙后要合上她的眼睛。九-九-藏-书-网
我能让他做些事情吗?就像他让我做出某些事一样?
他关上厨房门,把它锁起来,然后走回起居室,又朝外望去。圆脸警察已经回到了巡逻车里,但史蒂文斯依然站在驾驶座门边,有那么一瞬,赛德感觉史蒂文斯好像正直视着他的眼睛。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薄窗帘拉着,史蒂文斯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如果他真能看到什么的话。
问题:我知道麻雀是什么,或者它们意味着什么吗?
到工作的时间了。
突然,那篇该死的《人物》杂志稿件的一部分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毫无疑问,当他说出这句话时,那个黑心的狗杂种大吃一惊。如果这些描述符合实际情况,那么斯塔克在杀死米里亚姆前曾说过同样的话。
他用冷水反复冲洗伤口,直到手失去知觉,接着他从橱柜里取出一瓶过氧化氢。他发现自己的左手拿不住瓶子,于是他用左臂和身体夹住瓶子,以打开瓶盖。然后他把消毒剂倒进手上的洞形伤口里,咬紧牙关忍住疼痛,看着消毒剂变白起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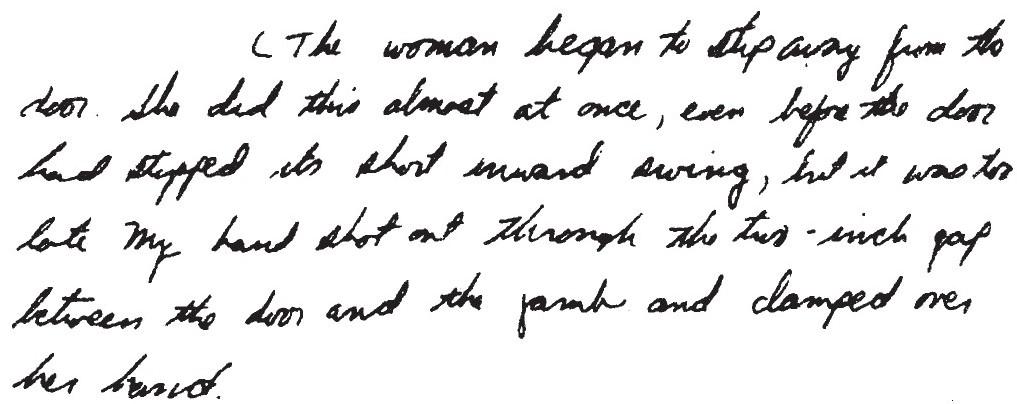
它们在这儿。它们是真的。怎么会这样呢?
“你在想用那玩意儿砸我的脑袋,对吗,小妞?”我问她,“我跟你说——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念头,你知道那些失去快乐念头的人们都怎么样了,不是吗?”此时,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窗户外,有一只鸟落在窗台上,正用它又黑又亮的眼睛盯着他看。
它们突然同时起飞,那些他记忆中来自老早以前的伯根菲尔德的鸟儿,那些在他位于拉德洛的家外面的鸟儿……那些真正的鸟儿。它们展翅高飞在两片不同的天空:一片是一九六〇年白色的春日天空,另一片是一九八八年黑色的夏日天空。
他终于找到了藏在一罐已经放了很久的剃须膏后面的塑料小瓶。赛德用牙撬开瓶盖,摇晃瓶子,把一片药倒在洗脸池的一侧。他考虑是否要再倒一片出来,最后决定还是算了。这种药效力很强。
麻雀的粪便,它们是什么一目了然,他想。
没错。你可以写上你的名字。你可以否认麻雀。很好。但你为什么要回来继续写呢?为什么这是如此重要?重要到足以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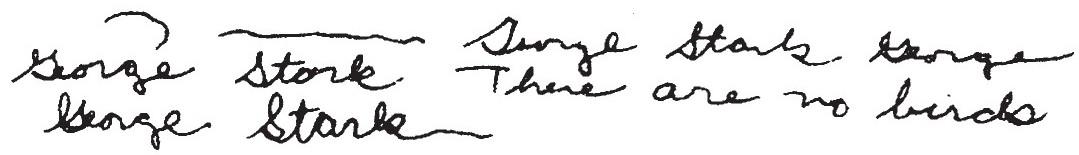
乔治·斯塔克,乔治·斯塔克。没有鸟,乔治·斯塔克。
赛德开始自问自答,这是他日记的一大特点。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习惯——这种找到他真正在想什么事情的方式——显示了另一种形式的双重性……或者这可能只是他精神分裂的另一方面,某种重要且神秘的东西。
当他再度控制住自己——或者说接近控制住自己时——赛德将日记本放回到写字台的抽屉里,关掉书房的灯,向下走到二楼。他在楼梯平台上驻足听了一会儿。双胞胎很安静。丽姿也是一样。
赛德将头向后一甩,咬紧牙关,忍住想从他的喉咙里逃出来的痛苦嚎叫。
赛德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正在阅读米里亚姆·考利谋杀案的描述……这一次,它不是一些支离破碎、令人困惑的词语,而是一个男人以他自己可怕的方式所做出的残忍流畅的表述,这人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作家——感染力强到足以让数以百万的人购买他的小说。

小妞
接着,他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这仿佛是世上最自然的进程(据他所知,可能确实如此),这个问题是如此基本,出现得如此自然,以至于他听到自己像参加作者见面会的羞涩书迷一般大声咕哝道:“你为什么要回来继续写呢?”
毕竟没什么需要用到它们的事情;它们是乔治·斯塔克的铅笔,而斯塔克已经死了……或者说是他这么认为。他想他最后会扔掉它们。
另一只麻雀降落,与其他三只麻雀挤在一起,在它们后面,他看到一整排的鸟停在车库顶上,车库里放着除草设备和丽姿的汽车。车库尖顶古老的风标上停满了鸟,它们的重量把风标压得摇摇欲坠。
他又停顿了片刻。是的,他写道,接着又写:不。既在又不在。当斯塔克杀害霍默·葛玛奇或克劳森时,我没有处在恍惚之中,至少我不记得有。我认为我所知道的……我所看到的……或许在增多。
“我们现在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先生?”
女人开始向门边闪去,她几乎是在门向内转动前就这么做了,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手从门和门框间的两英寸空隙中伸进去,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铅笔尖一触到纸页,他又把手抬起来,翻到新的空白页,并像之前一样用手掌将纸抚平。接着,铅笔回到纸页上写道:
他抬手想把铅笔放回去,却又停住了。他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望着他桌子左边的窗户。
赛德·波蒙特身体前倾,停顿了一下,然后在白纸顶端用正楷大字写下“麻雀又在飞了”。
问题:但我确实知道有麻雀。我知道这点,不是吗?无论艾伦·庞波或其他人怎么想,我知道有麻雀,并且我知道它们又在飞了,不是吗?
“不用。”赛德说,“我认为不用。我只是对听到的感到好奇。晚安,伙计们。”
他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他也认为这会让他再度变得易受伤害。下一次,可能就不是铅笔插进手里了。下一次,可能就是一把开信刀插进脖子里了。
他不想再读下去,不愿再读。他抬起胳膊,将他麻木的手犹如铅块一般一并举起。铅笔一旦离开笔记本,他的手就恢复了知觉。他肌肉痉挛,第二根手指的侧面感到钝痛;铅笔杆在他的手指上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凹印。
书房边有一个小浴室,当赛德觉得能走路时,他来到浴室,借着头顶刺眼的日光灯,检查自己手上剧痛的伤口。它看上去像是严重的枪伤——正圆的洞形伤口周围有一圈黑色的灼伤污迹。污迹看着像是火药,而非石墨。他把手翻过来,看到手掌一侧有一个针孔大小的亮色红点,是被铅笔尖刺伤的。
他走到厨房,给www•99lib.net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小心翼翼地不去弯左手。伤口热辣辣地疼。
他笑了。另一个警察没笑。“你今晚有点不安,波蒙特先生?”他问。
“你觉得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赛德问。
他向下扎去——斯塔克向下扎去——铅笔突然扎进了他左手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肉里。由于斯塔克用这支铅笔写字,所以石墨笔尖稍微有点钝,但它几乎穿透了那块肉。铅笔折断了。一汪鲜血注满了笔杆在他手上压出的凹印,突然那股控制他的力量消失了。他把插着铅笔、感到剧痛的手放在写字台上。
与《人物》杂志的麦克·唐纳森交谈,讲述一个关于斯塔克诞生的半虚构故事时,他想也没想就把地点改到了位于拉德洛的大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拉德洛写的,将场景设在这儿很正常——尤其是在你虚构一个场景、想象一个场景的时候,就像创作一篇小说。但乔治·斯塔克初次露面并非在这里;他不是在这里第一次用赛德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尽管以斯塔克或他自己的名义发表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们大部分奇怪的双重生活都是在这儿度过的。
在他的想象中,他从未怀疑过这点……但没有时间考虑它,没有心思考虑它。突然,书房不见了,他看到了伯根菲尔德的瑞奇威地区,他是在那儿长大的。那儿就跟他的斯塔克噩梦中的房子一样安静、荒芜。他发现自己正凝视着一个死去的世界里的一片寂静郊区。
形象出现了……但它扁平而不真实,只是脑海中一幅毫无生气的图画。当他开始动笔时,经常是这样——一种枯燥乏味的练习。不,比那更糟糕。他总觉得刚开始写时有点恶心,就像舌吻一具尸体。
他把这个念头放在大脑的前部,努力想要看清楚它。然后他再次抓起铅笔,开始把它放到下面的日记本上。
他又倒出四片止痛药,塞进裤子口袋中,把瓶子放回摆药的橱柜架上。接着他在伤口上贴了一块邦迪。看看这张圆形小塑料贴,他想,你不知道这玩意儿贴上去有多疼。他给我设了一个陷阱。他脑子里的一个陷阱,而我正好落入其中。
1
铅笔正在自动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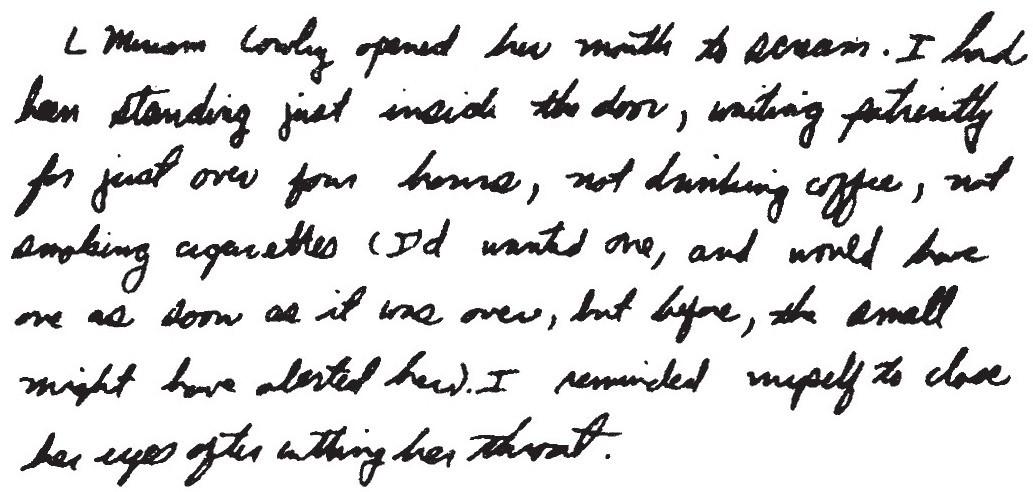
十字与大叉。
家就在开始的地方。
但他知道人们记录并相信许多类似的神秘事件,至少当它们发生在双胞胎身上时;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联系则更为怪诞。大约一年多前,一本新闻杂志曾登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由于他自己的生活中就有双胞胎,赛德很仔细地读了那篇文章。
问题:我在那儿吗?当他谋杀他们时,我在那儿吗?
问题:斯塔克知道他有一个痛处吗?一块脆弱的地方?
他关上抽屉,看着瓶子。第一次处在恍惚状态中时,他用其中一支黑美人铅笔在《金毛狗》的手稿上写下“麻雀又在飞了”,之后他就把瓶子扔进了抽屉里。他从来没打算再用瓶子里的铅笔……然而就在前几天晚上,他又在摆弄一支铅笔。此刻,它们就在这里,插铅笔的瓶子就摆在十几年来它一直摆的位置,在这十几年里,斯塔克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驻扎在他的体内。很多时候,斯塔克都很安静,几乎像是不存在。但一个念头闪过,老奸巨猾的乔治便会从他的脑袋里跳出来,犹如一个失控的玩具盒。啪!我在这儿,赛德!我们走吧,老伙计!准备出发!
这样的话,家一定就是指罗克堡。罗克堡,恰好也是故乡墓园的所在地。故乡墓园,在赛德看来,大约两个星期前,乔治·斯塔克就是在那儿初次以残忍的肉身出现,即使艾伦·庞波不这么认为。
但它没有完全死去,因为每栋房子的屋顶上都站满了叽叽喳喳的麻雀。每一根电视天线上都挤满了麻雀。每一棵树上都停满了麻雀。它们排满了每一条电话线。它们站在停着的汽车顶上,站在杜克大街和马尔伯勒巷拐角处巨大的蓝色邮筒上,站在杜克大街便利店前面的自行车的车架上,他小时候常去那儿替他妈妈买牛奶。
但它们没有。鸟儿们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他和斯塔克之间的交流依然完整可行。赛德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但他就是知道。
问题:威廉知道他有瘀青吗?
某部卡通片中的一句台词进入他的脑海,挥之不去:艾尼—梅尼—切里—比尼,灵魂马上要说话了!如果丽姿出现,问他手持铅笔,面朝白纸,在午夜前几分钟,坐在这儿干什么,他该怎么回答呢?说他正试图在火柴纸板上画一只兔子,以赢得纽黑文著名艺术家学校的奖学金?见鬼,他甚至没有一张火柴纸板。
它潦草地写完最上面一行,跳过两行,缩进一些,以斯塔克特有的方式另起一段,写道:
回答:是的,我认为你会发现它们完全一样。我认为这类似指纹事件。我认为这类似声波纹事件。
那是一只麻雀。
回答:是的。
赛德走到外面。他一打开厨房的纱门,两名警察就一边一个从车里走了出来。他们非常魁梧,动作像豹猫一样轻盈。
小路在半圆月忽明忽暗的光照下像黑色玻璃一般闪闪发光。他能看到路面上星星点点的白色污迹。
那些日子,我们夏天很晚才去湖边的房子,因为我在教授一门为期三周的课程——这门课叫什么来着?创造性方式。非常愚蠢的课程。那年七月末,我记得自己上楼到办公室,发现没有色带了。见鬼,我记得丽姿抱怨说连咖啡都没有了——
这一次,铅笔自己停止了移动。他举起它,低头看着潦草的字迹,它们冷漠而尖刻。除了家。我到那儿时就会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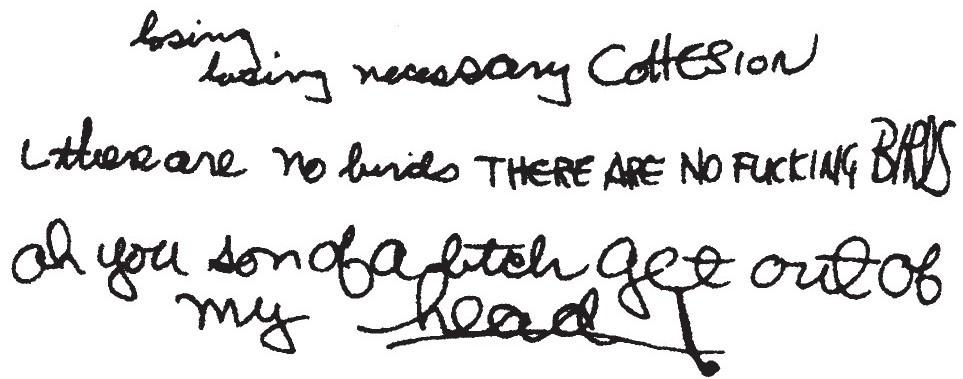
失去,失去必要的凝聚力。
没有鸟。他妈的没有鸟。
啊,你这个狗杂种从我的脑袋里滚出去!
这个抽屉又宽又深。他从中取出自己的日记本,接着一直将抽屉往外拉到头。他用来插贝洛牌黑美人铅笔的大口玻璃瓶一路滚到抽屉的最深处,其中的铅笔都掉了出来。赛德把瓶子拿出来,放到它平时的位置,然后收好散落的铅笔,把它们插回到瓶中。
回答:是的。www.99lib.net
“哦,我的上帝。”他重复道,听到自己的声音从一百万英里之外传来,一个充满了恐惧和极度惊奇的声音。“哦,我亲爱的上帝,它们是真的——这些麻雀是真的。”
问题:斯塔克知道有麻雀吗?
出了什么事情,乔治?你失去了你的一些快乐念头吗?
“我将一页纸卷进我的打字机里……接着又将它卷了出来。我所有的书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乔治·斯塔克却受不了打字机。或许是因为在他服刑的监狱里没有打字课。”
现在——天哪!又来了。文字又从他自己的拳头下涌出!上帝啊!
他不知道。
问题:知情者是谁?拥有麻雀的人是谁?
“嗯,我告诉你吧。”圆脸的警察说,“我不知道。我的观鸟课没及格。”
“没有——没有电话。”赛德说,“我在书房写作时,好像听到了一群鸟起飞的声音。这有点吓到我了。你们听到了吗?”
他把过氧化氢放回去,接着又从橱柜里逐一取出几瓶处方药,仔细阅读它们的标签。两年前他在跨越国境的一次滑雪中摔了一跤后,背部严重痉挛,善良的老医生休姆给他开了处方止痛药。他只吃了几片。他发现止痛药打乱他的睡眠周期,让写作变得很困难。
如果鸟儿们又回来了呢?
赛德慢慢沿着柏油小路往前走,一直走到他书房窗户的正下方。一辆卡车从地平线开上来,朝着房子的方向疾驶下十五号公路,有那么一瞬,车灯照亮了草坪和柏油小路。在一亮之间,赛德看到路上躺着两只麻雀的尸体——三叉状的脚爪戳在一堆羽毛外面。然后卡车开走了。在月光下,死鸟的尸体再度变成了两块不规则的阴影——仅此而已。
这里,斯塔克强迫米里亚姆给赛德打电话,他替她拨了电话号码,因为她吓得忘掉了号码,虽然曾经有几个星期她经常打这个电话。赛德觉得她的遗忘和斯塔克的理解既恐怖又可信。这时,斯塔克正用他的剃刀——
他在下面写道:
接着又有一只。
回答:我是知情者。我是拥有者。
他从衬衫口袋里取出斯克瑞普托牌钢笔,翻开日记本,拔掉笔套,犹豫了一下,接着写道:
乔治·斯塔克用铅笔写作的习惯纯粹是缘于赛德忘了把色带带到他位于罗克堡的夏季别墅的小办公室里。他没有打字机的色带,但灵感却不断涌出,于是他在小写字台的抽屉里翻来翻去,最后找到了一本笔记本和几支铅笔——
赛德完全同意这种猜测。他花了二十四小时才鼓起勇气接受这个想法。
铅笔在鸟形曲线下面写道。
他不能这么做。他需要我。
“他又打电话来了吗,波蒙特先生?”从驾驶室这边出来的警察问。他名叫史蒂文斯。
疼痛好一些了,但震惊之后——所有那些震惊之后的余波仍在,他觉得自己要过一会儿才可能睡着。于是他走到一楼,透过起居室大窗户薄薄的窗帘,瞥了一眼停在外面车道上的州警察巡逻车。他能看到车里闪烁着两支香烟。
他的胳膊突然扬起。同时他麻木的手轻弹了一下铅笔,灵活得犹如一位表演牌技的舞台魔术师,他没有用手指握住铅笔杆的下半部,而是将它攥在拳头里,仿佛它是一把匕首。
铅笔抖了一下,接着在最后一条信息下面潦草地画了一道长线,看上去就像是声波纹。
赛德读到这则报道时,既没有相信也没有不相信。它和异教偶像崇拜或钻孔以缓解头痛一样,离他自己的生活非常遥远。现在它似乎拥有了自己的致命逻辑。可他不得不召唤麻雀。
他也不知道。但他确定一件事:今晚来的麻雀,那些恰好在他陷入恍惚状态前来的真麻雀,只是所有可能来的麻雀中的一小部分。或许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
此时笔在纸上飞速划过。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如此快速或自然地写过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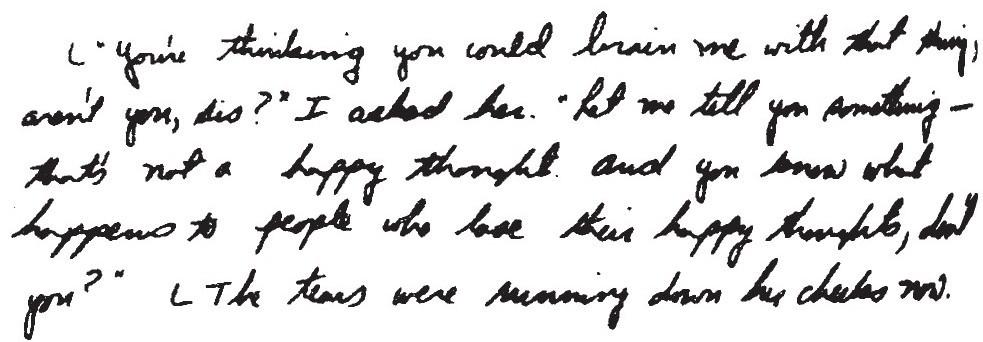
然后铅笔像一台气喘吁吁的机器似的停了下来。
有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远隔重洋——但当他们中的一个左腿骨折时,另一个尽管根本不知情,却也感到左腿剧痛。有一对同卵双胞胎姐妹创造了一种她们自己的语言,一种这世上任何其他人都不认识和理解的语言。这对双胞胎姐妹虽然智商都很高,但她俩都不曾学会英语。她们需要英语干什么呢?她们互相拥有……她们只需要这点。这篇文章还写道,有一对出生便分开的双胞胎,成年后相聚时却发现他俩在同年同日与两名同姓且外貌极其相似的女人结婚。而且,两对夫妻都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罗伯特。两个罗伯特还是同年同月出生的。
在《马辛的方式》中,家是指弗拉特布什大街,亚历克西斯·马辛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清扫他生病的酒鬼父亲的桌球房。这个故事里的家是在哪里?
赛德冷静地看着他。“是的。”他说,“最近,我每天晚上都感觉不安。”
短刀与短剑。
当他在丽姿身边躺下时,丽姿没有醒。过了一会儿,他逃入梦乡,断断续续睡了三个小时,期间无可控制的噩梦总是萦绕他。
谋杀案发生时,我进入了他的脑子——我就在他的脑子里。所以在戴夫市场我们的谈话中,我使用了同样的语句。
它差一点就要刺穿皮肉了,他想。
他又停顿了片刻,接着他写道:
问题:我确信自己相信他吗?
你在哪里,乔治?他想。我怎么会感觉不到你呢?是因为你像我没有意识到你的存在一样,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吗?还是有其他原因?你他妈的到底在哪里?
回答:是的。我认为他知道。
他想到麻雀。他试图唤来所有那些鸟的形象,所有那些成千上万只的鸟儿,在春天温和的天空下,它们站在屋顶和电话线上,等待心灵感应的信号一出现便展翅高飞。
聪明,非常聪明。但这不完全符合事实,不是吗?这不是赛德第一次讲一个与事实仅有些许关联的故事,他想这也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当然,前提是他能熬过这个难关。这不完全是说谎;严格来说,它甚至不是为事实添油加醋。它几乎是一种把自己的生活小说化的无意识行为,赛德不知道哪个小说家是不这么做的。你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美化自己;有时这确实有美化的作用,但你也容易讲一个会丑化你、让你显得滑稽蠢笨的故事。是在哪一部电影里,一些新闻记者说“当你要在事实和传奇之间做选择时,选择出版传奇”?可能是《双虎屠龙》。这也许会导致不道德的低劣报道,但它能创造出色的小说。虚构你自己的生活几乎是讲故事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就像弹吉他会让你的指垫长老茧、多年抽烟会导致咳嗽一样。九*九*藏*书*网
铅笔触及纸张,开始写起来。
一半与另一半。
他把手伸向大口玻璃瓶,接着又缩了回来,仿佛是从一个熊熊妒火燃烧的火炉边缩回来似的。
我想知道我是否能接入他现时的活动记忆……他有意识的思绪。
他们坐在那儿,冷静得犹如夏日里的两根黄瓜,他想。鸟儿们没有打扰他们,所以或许除了我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鸟。毕竟,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被打扰。
然而,这种感觉挥之不去。
他已经做了他想做的事情:联系并进入斯塔克的脑子,正如斯塔克已经进入了赛德自己的脑子一样。但谁能猜到他这么做会触及什么样的未知残暴力量呢?谁能猜到呢?麻雀——意识到麻雀是真的——已经很糟糕了,但现在的情况更为糟糕。他感觉到铅笔和笔记本碰上去都很热吗?毫无疑问。这家伙的头脑他妈的就是一个火炉。
问题:是谁写到了麻雀?是谁用血写的?
但他其实非常明白。他将试图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一个明显到他甚至都不屑写下来的问题:他能有意识地引发恍惚状态吗?他能使麻雀飞起来吗?
如果威廉哭,温迪就会哭。但我发现他俩之间的联系远比这要深刻与紧密。昨天温迪从楼梯上摔下来,碰伤了——一块看上去犹如一个巨大的紫色蘑菇的瘀青。当双胞胎从小睡中醒来时,威廉身上也出现了一块瘀青。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形状。
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当他在克劳森和米里亚姆家的墙壁上写下“麻雀又在飞了”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干完后也不记得这事了?
“你是什么意思?”赛德嘀咕道,但他感到殷切的希望在他的脑中爆开。可能就是这么简单吗?他认为是可能的,尤其是对一个本来就无事可做的作家而言。天哪,现实中的很多作家不写作都没法活,或者说他们感觉没法活……像厄内斯特·海明威那样重要的人,写作和存在真的是一回事,不是吗?
“我黑暗的另一半。”他咕哝道。
“晚安。”圆脸警察说。
自动书写这种事情他在有关通灵的报道中读到过,但从来没有见过。试图用自动书写的手段联系一个死灵魂的人,用手松松地握住一支钢笔或铅笔,笔尖抵在一张白纸上,就这么等待着灵魂来移动他的手。赛德读过的文章说,在显灵板的协助下从事自动书写,常被当成玩笑,甚至是一种派对游戏,但这可能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它可能容易让从事者走火入魔。
家就在开始的地方。
他相信这事结束之前,它们会回来。
在他看的时候,另一只鸟加入进来。
止痛药显然还没有过期失效,它开始起作用,赛德手部的疼痛开始缓和了一点。如果他不慎弯弯手,就会痛得叫出声来,但如果他当心点,就不会疼得太厉害。
2
他啜了一口牛奶,看着食品储藏室的门。
赛德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用笔的一端敲击日记本的纸页,思考着这个问题。然后他再度俯身向前,开始更快地写。
他写道:他一定认识我。他一定看得见我。如果他真的写过那些小说,那么他已经认识我很久了。而且他自己所知道的,他自己所看到的,也在增多。那些追踪和录音设备一点儿也没让老奸巨猾的乔治烦恼,是吗?没有——当然没有。因为老奸巨猾的乔治知道它们会在那儿。你花了差不多十年写犯罪小说,不会不知道那样的事情。这是它们没能让他烦恼的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更好理解,不是吗?当他想要跟我谈话,跟我私下谈话时,他完全知道我会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我,不是吗?
赛德又拉上薄窗帘外的厚窗帘,然后朝酒柜走去。他打开柜门,拿出一瓶格兰利威,这一直是他最喜欢的烈酒。他非常想要喝一杯,但这会是再度开始喝酒的最差时间。
再也别这样了,他想。请再也不要这样了。
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念头,但书房是在房子的另一侧。它的窗户从车道是看不见的。在那儿也看不到车库。所以警察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看到鸟。至少当它们开始下落歇息时,他们是看不见的。
是我召唤了它们,还是我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它们?
没错,但他发疯了。疯子有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自己最有利。
“没关系。”马辛告诉杰克·兰格雷,“所有的地方都一样。”他停了一下,“或许除了家,我到那儿时就会知道了。”
赛德喝完牛奶,冲洗一下杯子,把它放进洗碗机里。接着他走进食品储藏室。这里,右边的架子上放着罐头食品,左边的架子上放着纸包装食品,在两边的架子之间有一扇通往后院草坪的两截门。他打开门锁,将两截门推开,看到野餐桌和烧烤架立在那儿,犹如沉默的哨兵。他走上外面的柏油小路,这条小路围绕房子的这一侧延伸,最后与房前的主干道会合。
他的手的第一动作又是抬起来,翻到日记本上新的一页。手又垂下,将纸页抚平……但这次铅笔没有立刻开始写字。赛德一度以为那种联系(不管它是什么)已经中断了,虽然他的手依然麻木,这时他手中的铅笔猛地一动,仿佛它本身是一个活物……活着,但受了重伤。它猛地一拉,在纸上留下一个困倦的逗号,又猛地一拉,画出一条破折号,接着它写道:
回答:我不知道。但是……
回答:知道麻雀的人。拥有麻雀的人。
但现在似乎他终究又用得到它们了。
所有的地方都一样。他先认出了这句话,然后是整段引文。它来自斯塔克的第一本小说《马辛的方式》的第一章。
真是这么回事吗?赛德不知
藏书网道,不敢肯定,但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不想此事重演。他低头看看字迹潦草的纸页,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一种说不出来的惊讶。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再次把铅笔放下来,他不愿再去完成他和斯塔克之间令人厌恶的交流……但他开始这么做并不是单单为了听斯塔克亲自描述米里亚姆的谋杀案,不是吗?
他望着食品储藏室的门,思考该如何走进去……以及如何从那儿再走到外面,走到房子的另一侧去。
这件老古董的上方挂着三盏玻璃灯罩的灯,当赛德像现在这样只打开这三盏灯时,它们投射在凌乱桌面上的刺眼的重叠光圈会让人觉得他仿佛是要开始玩某种奇怪的弹珠游戏——在如此复杂的桌面上玩要遵循什么规则,谁也说不清楚,但温迪摔跤后的这个晚上,旁观者可以从赛德紧绷的脸上猜出游戏的赌注极高,不管规则是什么。
他来的时候有点迷糊,他啜着牛奶想。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他恢复清醒的速度快得吓人——但他来的时候确实有点迷糊。我想他是在熟睡。他可能梦到了米里亚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接入的场景太过连贯了,不可能是一个梦。我认为那是记忆。我认为那是乔治·斯塔克潜意识的记录,一切几乎都是写下来的,接着对号入座而已。我想象如果他接入我的潜意识——就我所知,他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他会发现同样的东西。
赛德抽出一支铅笔,看看木头笔杆上浅浅的牙印,然后又把铅笔叮当一声扔回瓶中。
我做到了,他迷迷糊糊地想,用左手擦去他嘴边和下巴上的唾沫。我做到了……我希望自己能顺其自然。这是什么?
他低头凝视着从他的拳头之下涌出的文字,心脏剧烈地跳动,感觉好像要从他的喉咙里跳出来。写在蓝线上的句子是他自己的笔记——不过所有的斯塔克小说都是他亲手写的。他俩有着同样的指纹,同样的香烟口味喜好,完全同样的声音特点,要是笔迹不同,倒是奇怪了,他想。
“他一定看得见。”赛德含糊不清地小声说。
但他决定还是吃药试一下。肯定是要处理的——疼痛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至于医院……他又看看手上的伤口,心想,我大概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但如果去的话我就完了。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有太多人像看疯子一样看我了,足以让我永生难忘。
史蒂文斯只是点点头。他宽帽檐下的眼睛明亮却毫无表情。
也许它们已经失效。也许你可以靠狂笑一通或上医院来终结这个疯狂可笑的夜晚——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乔治·斯塔克非虚构类的处女作,他厌恶地想。
赛德不知道从乘客座一侧出来的警察叫什么。他是一名年轻的金发男子,长着一张透着善良天性的无邪圆脸。“我听到也看到了。”他说着指指房子上方挂着月亮的天空。“它们横穿月亮。麻雀。很大一群。它们极少在晚上飞的。”
但当它们都飞起来时,他们会看见吗?你想跟我说他们都没听见动静?你看到了至少一百只鸟,赛德——或许有两三百只。
问题:如果你把我孩子们腿上的瘀青拍成幻灯片,然后将片子重叠在一起,你是否会发现两者完全一样?
他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一个重新装修过的宽敞的阁楼——它被分成两个区域:读书区和工作区。前者除了摆满了书,还放着一张沙发、一把躺椅和一盏伸缩灯;位于长形房间另一头的工作区则摆着一张毫无美感的老式写字台。它又破又旧,却是一件非常实用的家具。赛德从二十六岁起就拥有了这张写字台,丽姿有时跟大家说他不愿意扔掉它,是因为他私下里认为它是他自己隐秘的词汇源泉。当她这么说时,他俩都会微笑,好像他们当真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赛德打了个冷战,走回房子里。他像一个窃贼似的溜进他自己的食品储藏室里,锁上门,然后带着剧痛的手上了床。上床前,他就着厨房水龙头的自来水又吞下一片止痛药。
他将日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把笔放到一边。心脏剧烈地跳动,皮肤因恐惧而冰冷,他伸出颤抖的右手从广口瓶中抽出一支贝洛牌铅笔。在他的手中,铅笔似乎正以一种令人不快的低温燃烧着。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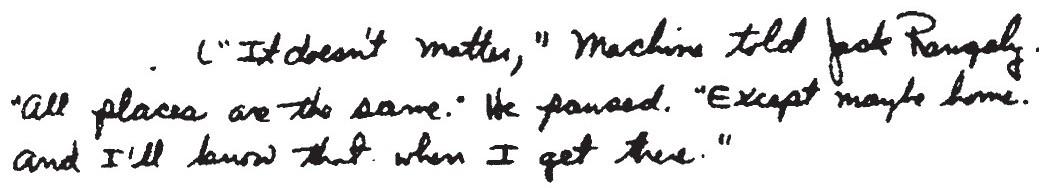
他究竟想用这支铅笔干什么?
斯塔克的诞生其实和《人物》杂志上的描述相当不同。用铅笔写斯塔克的小说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决定,虽然时间已经将它变成了一种仪式。说到仪式,作家们和职业运动员一样迷信。棒球运动员可能会日复一日地穿同样的袜子或在走上击球位置前在胸口划十字,如果这么做时他们曾击出好球;成功后的作家也倾向于遵循同一套模式,直到它们成为一种仪式,以避免出现类似击出坏球的灵感枯竭期……即所谓的作家心理阻滞状态。
回答:是的。
赛德·波蒙特靠在办公椅上,嘴角边泛出一点唾沫,两脚无目的地抽动,现在书房所有的窗户都站满了麻雀,它们犹如奇怪的鸟类目击者,全都盯着他看。他的嘴里迸出一声长长的咕噜声,两眼上翻,露出凸起的闪耀眼白。
那个人认为我有罪,赛德一边想,一边往回走去。有什么罪呢?他不知道。大概也不在乎。但他长着一张认为人人都有罪的脸。谁知道呢?或许他是对的。

崩溃。
家就在开始的地方。如果这依然是斯塔克的想法,如果这句双关语确有意思,那么它指的就是这里,这栋房子,不是吗?因为乔治·斯塔克就出生在这里。
但他明白,如果他坚持写下去,如果他不停地在纸上写字,情况就会不同,某件既美妙又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作为个体的单词开始消失。索然无味的僵硬人物开始活络起来,仿佛他们被他在一个小壁橱里关了一夜,在开始跳复杂的舞蹈之前必须先活动一下筋骨。他的脑子里开始发生变化。他几乎能够感觉到脑电波的形状变了,摆脱了他们谨小慎微的正步束缚,变成了多梦睡眠中柔软不羁的三角波。